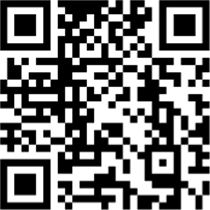张国焘叛逃时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
发布时间:2024-03-26 02:58:32 来源:胸类
从某种程度上说,张国焘是被王明的一番话吓跑的,听起来比较儿戏,但这就是实际情况。
王明之所以能让张国焘这么害怕,并不是王明长得有多么吓人,而是从王明嘴里说出的“托派”让张国焘不自觉的神经紧绷。
王跟张国焘说,李特和黄超已经被定为托派分子处决了,话里话外也有将他定为托派分子的倾向,面对死亡的惶恐感立马传遍了张国焘全身,脑瓜子嗡嗡的。
在十二月会议上,王明不仅否定了洛川会议上的观点,不点名批评了教员主张的“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”之外,还着重讲了中国托派的问题。
陈独秀是托洛茨基钦定的中国托派领袖,因为跟托派的关系太过紧密,直接引发陈独秀的后半生变得很敏感,极少有人提起。
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其他中国托派组织的成员,基本都是受到了托洛茨基写的《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》、《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》这两篇有关中国的文章影响,才选择追随托洛茨基。
陈对这两篇文章奉为瑰宝,因为这两篇文章,帮他完美解决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划分和归属问题。
托当时为了反击斯大林和布哈林,在文章中直言不讳:“苏联布尔塞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,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,反对之独立政策,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。”
陈独秀见到这样的说辞,犹如顿悟,拍案叫绝,当即就表示:“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一百的正确。”
托有关中国的文章不仅为陈独秀解了围,还在文章里为中国托派设计了相应的路线、方针,以及总目标。这也成了中国托派的理论基础。按理说,有了托的文章指导,中国托派应该能毫无阻碍的团结到一起,可恰恰相反。
1930年前后,中国主要有三个托派组织,分别是“我们的话”派、“十月社”和“无产者社”。
最先成立的是“我们的话”派,这是由一群被莫斯科遣送回国的留苏学生建立的,之后是陈独秀为代表的“无产者社”,最后成立的是以刘仁静为代表的“十月社”。
刘仁静一开始回国的目的,是代表托洛茨基,将中国的托派组织团结到一起,但“无产者社”和“我们的话”这两派互相看不顺眼,主要是“我们的话”派不愿意接纳陈独秀,嫌他不纯粹。
后来又发生了中东路等事件,陈独秀发表了不少文章批评“上海”,刘仁静看了这些文章后,觉得写得很有问题,开始转而批判陈独秀,最后刘仁静和一些老人又成立了一个“十月社”,跟先成立的两个托派组织打擂台。
因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“你左,我比你更左。”、“你坚持,我比你还坚持。”、“你纯粹,我比你还纯粹。”
看谁目的更纯粹,看谁原典阐述更精辟,看谁真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。凡变通的、调和的、修正的、妥协的一律严肃批判,无情打击。
这三个组织完美践行了这一点,互相看不上对方,都觉得自身的理论和想法才是对的,对方的都是垃圾,不断的分裂、争吵。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三派之间互相指责、相互批判,围绕着中国革命的性质、任务、方针、策略、形势判断、组织体制等等理论和问题展开了无休止的、多层面的争论。
他们的主要革命活动,就是开会、报告、争议、结论,将九成九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理论争论上,在各自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又一篇理论文章。基本没革命实践活动,所以实际影响力范围极其有限,也很小。
就连托洛茨基都直言,没搞明白中国这三派有什么实质性的分歧,为啥就不可以团结到一起呢?
最后还是托洛茨基亲自发话,并多次敦促,让这三派以陈独秀为领袖团结到一起,这三派才不情不愿的走到一起,成立了统一的组织。
到了抗日时期,1937年10月左右,陈独秀以中国托派领袖的名义,派罗汉来到延安商谈,想要参与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。
最后双方算是达成了一个基本合作框架,愿意脱离托派并承认自己在托派中错误的,能恢复党籍,不愿意的,也可以在党外合作一致抗日。
但王明和康生回到延安后,强烈反对接纳中国托派,对陈独秀极为敌视,并放话抗日和什么人都能合作,就不可以跟托派合作,还给陈独秀扣上了一个领日本津贴的污名。
张国焘当时回忆:“王明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,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,那还了得;如果斯大林知道了,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他还说反对托派,不能有仁慈观念,陈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。”
也不怪,年纪轻轻的王明,能在共产国际内部爬到这么高的位置,跟他极为敏感的政治嗅觉不无关系,的确有过人之处。
王明是常年待在莫斯科的人,他对斯大林反托派的手段和坚决态度是很清楚的,对被定为托派是什么下场,都是亲眼目睹的。此后,为说明反托派的重要性,王明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,举了非常多的例子,将话说得很重。
结果没想到,王明对反托派的极端重视,以及他对张国焘说的那番话,在张国焘那里发生了化学反应,直接促使张国焘下了叛党的决心。
王明在跟国焘交谈时,不仅说了黄超和李特,还说了俞秀松、周达文等人,这些人以前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跟王明等人争论过,后来跟张国焘一块到了列宁学院学习,毕业后辗转到了新疆工作。
而王明直白的告诉张国焘,这些人在莫斯科的几次清党中,都没有露出破绽,这次他到了新疆,将他们逮捕审问,果然都是托派,自然也只有把他们惩之于法了。
这些话,既带有威胁挑衅性质,也有几分“大仇得报”的扭曲之感,这让张国焘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:“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,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,使我受着极大的刺激。”
“由这种重大的刺激,我经过一番考虑,最后决定脱离。”这是张国焘写在明面上的叛逃理由。
将自己叛逃的原因归结于王明,是张国焘的一种托词,王明说到底还是外因,虽说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,但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最终的原因,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。
就好比鸡蛋需要适合的温度才能孵化,温度就是外因,但是不管温度多适合,石头永远都孵化不出小鸡。
对于张国焘叛逃内因的一些分析和见解,我们在上一篇文章里已经聊过了。(点击即可查看)
这种闲适是装出来的,张国焘就为了营造出一种松快的假象,好让人不再注意他,这样他就有充足的时间去思考最快离开延安的方法。
- 上一篇: 宝鸡绿壳鸡蛋孵化技术
- 下一篇: 武汉专家称高温天鸡蛋不可能孵出小鸡 纯属巧合